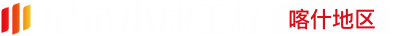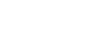一、旧貌新颜:从生活空间的改造到文化空间的重塑
喀什噶尔古城位于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的中心区域,因历史悠久,被当地人称为“喀什老城”。喀什老城以艾提尕尔广场为中心,分为东、西两个片区,总占地面积约1521亩,有常住居民4.91万人,维吾尔族居民占总人口的90%以上。
2008年以前,喀什老城作为一个普通的居民聚居区“隐身”于喀什市区中心,鲜为人知。部分喀什当地人甚至从未听闻,或从未关注过这片生土建筑群的存在:“以前,很多喀什人没有去过老城。我的丫头从出生到2008年上大学,都没听说过老城。”据喀什老城的居民回忆,改造前,人们的社会流动性很小,老城同时满足了生产生活、经济交易、社会交往等多种需要。“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当时,老城街面为未铺筑的土路,晴时扬尘,雨时泥泞。房屋多为2~5层的庭院式平顶建筑,部分人家挖有地下室。建筑材料多以生土为主料,辅以原木作为横梁、立柱、门窗和楼梯等,掺杂麦秸的草泥作为墙面涂料。因为建筑材料防寒效果不佳,冬春季节,人们习惯于烧煤炉取暖,空气中常见烟尘迷漫。缘于喀什地区处于帕米尔高原至天山南北地震带,地震频发,加之气候干燥,房屋多为铺就少量砖块的浅层地基,缺乏钢架结构的支撑,易于干裂倒塌。据当地人说:“以前,老城里没有水厕,水管也不入户,几十米范围内设有一个集中供水点,人们就拿着桶到那里打水。所以,有句话形容说‘污水靠蒸发,水管墙上挂’。”从田野材料看,许多当地人认为,改造前的喀什老城在用水、用电、排污、取暖、防火、抗震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便或安全隐患。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和旅游业的发展,老城人对改善人居环境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诉求日渐增强,老城的待客、社交和文化展示的功能日益凸显,旧城改造的任务迫在眉睫。
2008年6月,喀什市“老城区危旧房改造指挥部”组建,其下设的“老城区危旧房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老城办”)负责项目的执行工作。经过调研和评估,老城办初步确定了12290户住户的房屋涉及不同程度的拆除、重建、大修和保护。其中,拆迁户3000户,需拆除重建的2245户,涉及大修加固的7 008户,需加以保护的37户,总工程量约759281平方米。
然而,前期制订的改造方案并未得到老城居民的普遍认可。改造方案中的一个内容,是要求将居民住宅拆除重建为3~4层的楼房。楼房一层为商铺,二层以上为居民住宅。但是,当建立试点并召开宣讲会时,该方案受到了较大抵触。原因在于,老城人多年养成了院落式的生活习惯,喜好在庭院中央栽种植物,聚会聊天、观赏纳凉。当地人离不开泥土,离不开院落:“让我们上楼去,我们不习惯。我们的想法就是,房子在原地改造就可以了。这样,我的土地还在,我的房子还在,我的邻居也还在。”
居民的需求并不是从“旧屋”到“新屋”的机械式改造过程,而是在人居环境改善的基础上,留住一个由人、物、建筑、记忆、情感共同建构的文化空间。除了房屋本身,人们更离不开的是儿时一起捉迷藏的“秘密通道”,至今仍爱召唤自己小名的邻居大叔,以及手艺人“叮叮当当”钉马掌的听觉记忆。对于人、事和场景的感官记忆和童年经验的养成,使人们生活、成长的居住空间同时兼为文化场域。“人与物体互动所产生的感觉,与抽象的思维、体验相联系,抽象的想法会将其构建为强大且有指向性的体验。”童年记忆中的往事虽时过已久,但文化空间中的人、物件和场景,仍能清晰地唤起人们关于旧人、旧物、旧事的情感体验,产生联觉的(synaesthetic)感官记忆。所以,旧城改造过程中,对待文化传统的发展变迁,不能简单采取革故鼎新的态度,还应考虑到历史和情感的延续性。老城人在老城文化的滋养中长大,他们既是老城文化的缔造者,也是文化持有者和文化变迁的推动者。旧城改造不是简单地将资金转化为建筑物的更新换代,更应考虑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事实上,场所精神(genius loci)比建筑本身更需要保护。”只有将对“人”的观照融入“城”的改造中,才能使“人”有情感,“城”有温度。
经与老城居民的进一步沟通协商,老城办制订了“一户一设计、一户一改造”的项目方案,并邀请到一位素描师进行房屋测绘。素描师需要挨家挨户了解人口结构、居住习惯、功能需求、审美偏好等,并为需要拆除重建及大修的居民进行“一户一测绘”。因住户需求各异,家庭成员意见不同,协商次数最多的一户达60余次。
2010年6月,喀什老城改造项目得到了国家及自治区补助共计70951万元,居民又自筹约16173万元,改造施工环节正式启动。施工过程中,部分居民需要过渡性迁出6至12个月不等,政府为其提供相应的补贴。
2015年1月,老城中居民住宅的主体部分改造完毕。房屋建筑的抗震能力达到设防烈度8度(震级约为6.5级)的标准,室内引入自来水、天然气、壁挂炉,实现了卫生间入户,既解决了饮用水、燃气和取暖等问题,又避免了燃煤、燃柴隐藏的安全隐患和烟尘污染。在建筑外观的涂料选用上,采用了具有防火、防水、保温功能的材料。这种涂料原本为白色,为了保持生土建筑群的地方性特色,施工方在其中加入了泥土和麦秸,将建筑外墙统一为草泥色。门、窗、回廊、屋顶部分和室内装修装饰等细节设计由居民自主完成。
当地人作为文化场域中的“我者”,对当地文化的认知和经验具有权威性,了解哪些部分可以拆除,哪些细节需要保留。部分老城居民在改造前便将旧门窗、旧楼梯、旧屋顶、旧回廊等拆卸留用,待建筑主体建成后再重新使用,保留了老宅的古旧特征。“留住乡村不是为了抱残守缺,不是为了留住‘落后’,不是为了继续维持其作为现代性对立面的地位,而是如何在它赖以维系的经济被吸纳到现代经济之后,让它继续发挥家园和传承文化的作用。”个性化的审美处理发挥了居民的主体性作用和创造力,保证了文化的延续性,避免了因改造造成的文化流失,留住了老城人成长中的感官记忆与乡愁,不仅保持了老城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还体现了不同元素在同一文化场域内的“和谐共生”。美国社会学家伊芙琳·佩里(Evelyn M.Perry)认为,在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承认差异、接受不同”成为文化和谐共生的基础。
为了使改造后的老城既宜居,又宜业,老城改造不仅要改善居住环境,还要促进经济发展,完成社会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喀什市政府提出了“老城改造完成之时,就是申报5A之日”的目标,明确了喀什老城向旅游风景区转变的发展方向,强调了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对景观重塑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旅游业的创新发展做好物质、空间和文化上的准备。截至2020年7月,喀什老城的空间改造仍在继续推进,在保留了原生的花盆巴扎、帽子巴扎、蔬菜巴扎、手工艺巴扎等功能分区的同时,还打造出印象街、九龙泉公园等新的文化街区。
二、转型之“旅”: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与交互
2015年2月,喀什老城改造的主体工程完工。喀什老城从当地人的生活区“华丽转身”成为国家AAAAA级旅游风景区。成为旅游景区之后的老城,不再只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还兼具展示、接待、商品交易和文化交流等功能,游客数量和商铺数量逐年增加。根据《2017年喀什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1月)》显示,“全年接待游客422.2万人次,旅游收入26.1亿元,分别增长19.2%、15.3%”。《2018年喀什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1月)》显示,“喀什市旅游呈现‘井喷式’增长,2018年共接待游客552.9万人次,旅游收入37.6亿元,同比增长31%和43.7%”。《2019年喀什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显示,“全年累计接待游客880万人次、旅游收入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27%”。根据笔者的走访调查,截至2019年9月,喀什老城中开设的商铺共计974家。其中,老城东片区共575家,西片区共399家,经营手工艺品及相关衍生品的商铺超过300家。
游客数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一家酒店的负责人阿地力江·艾力芳说:“老城改造以前,我们的客人基本都是本地人。2017年以后,喀什旅游一下子发展起来,游客多了好多倍。”土陶艺人祖力甫卡尔·阿巴拜克力和师父吐尔逊·肉斯塔木在老城中开设了“泥巴艺术工作室”,祖力甫卡尔·阿巴拜克力说:“以前,师父制作、烧制和销售土陶都在自己家里,那时候游客很少,停留时间也短,更不会到家里来。这样的话,土陶艺人只能靠商家收货,价格被砍得很低就拿走了。现在我们自己在老城开了店,就可以直接和游客交流了。”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市场的繁荣作为反映社会关系的风向标,在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学家科塞(Lewis·A.Coser)所说的“社会安全阀(social security valve)”的隐喻作用。
旅游业的兴起还催生了新的文化产品的开发。2018年,车长征转行经营起老城中第一家文化剧场。他说:“我们创作的这台演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的舞蹈文化。它不仅是一种舞蹈,也是一种庆祝方式,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但是,将生活中的艺术搬上舞台,需要进行大量艺术加工和再创作,我们咨询了不少编导和文化学者,如何使演员的表达更加舞台化、舞蹈的表现力更强。”演艺类文化产品的开发,常以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形式为原型或素材进行改编或再创作。它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听觉、视觉、感觉等多种方式调动观者产生情感体验,加深对地方性文化的感受和理解。这就要求创作者对当地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针对旅游市场,创作出符合游客审美需求的作品。因此,文化产品的开发不仅具有商业属性,还兼具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
人员的频繁流动、交往和互动还带来文化观念的博弈。一位游客对当地文化的交叉融合现象表现出疑惑:“前段时间新开了一个民宿,本来当地人睡的是炕,但这个民宿在炕上又支了两张床。他说,游客过来,睡不习惯炕,要睡床。结果,游客来了,把鞋脱了以后上炕,上完炕还要再上到床上。”旅游业是外地人进入当地,以及当地人接触外界的一个“窗口”行业。旅游使不同文化在同一地域空间中发生接触,并进行调适,为多文化之间产生涵化(acculturation)提供了可能性。“用床还是用炕”的争论成为地方性文化与外来文化博弈交锋的一个例证。
旧城改造后,环境卫生问题得到了较大改善,当地人的卫生习惯也悄然改变。喀什老城的油画家买买提江·纳斯尔丁说:“有一天,我坐在画室门口,看到一个二三岁的小孩,个子小小的,骑着车子过来扔垃圾。我一看,他的袋子刚好掉到垃圾箱里。喀什人的素质正在提高,从这个小娃娃就能看出来。”人与环境的影响作用是相互的。
除了老城中的“人”在变化,“物”也发生着角色转型。因为场景、场域和语境的不同,一件物品可能同时兼具多种功能,它们的身份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语境中发生转换。一度作为老城人生活用品的喀什土陶,受到工业制成品的冲击,替代性产品大量出现,传统土陶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大幅缩减。而随着旅游业发展,土陶被推入旅游市场,成为旅游纪念品。买买提江·纳斯尔丁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妈妈来学校送饭,就拿上一个土陶碗,一个木头勺子。后来出现了塑料的、金属的、瓷的,做的很好看,质量也很好,土陶就不用了。(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那时候花盆巴扎的生意特别不好,一个碗都卖不出去。最近几年游客来了,对传统手工艺品很感兴趣,他们的生意又变好了。现在一个瓷碗、玻璃碗只要几块钱,土陶碗反而要几十块钱了。”
文化市场与旅游市场的繁荣,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具有一定文化代表意义的喀什土陶,从日用品店走进了旅游纪念品店和艺术收藏品店,从日用陶器逐渐转变为人们装饰生活空间的艺术陶器,面对的主要受众从当地人转向外地游客,在市场中的销售价格也因而提升。旅游市场重塑了“物”的价值体系,使“物”的定价不仅取决于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作为旅游纪念品的“物”,除了具有物质本身的实用价值外,还承载着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情感联系,促使人们睹物思人、触物生情。“‘触物’就是‘人与物’的关系,‘生情’就是‘人’对于‘物’的反作用。”“自在之物”与“纪念之物”“典藏之物”的区别,在于“物”所承载的情感体验。作为旅游纪念品的物,其造型、色彩、花纹图样及人们购买时的情境等,都可能唤起购买者的记忆和情感反应。
为了使旅游体验更直观,旅游目的地还开发出体验式旅游项目,它将游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使旅游体验更有深度。买买提艾力·玉素普是位于喀什市区近郊的一家土陶作坊的负责人,作坊生产的土陶制品主要面向商户进行批发,但近年来常有游客慕名而来进行学习和体验,尤其是寻求深度游的背包客和选择自驾游的客人,更偏爱参与感较强的旅游过程。
体验式的旅游方式使“喀什游”不仅局限于购物、观光和休闲,还使旅游者的参与更具整体性、多元性和体验性。深度的文化体验既拉长了游客的在地时间,还拉近了客地关系。同时,文化体验逐渐发展成为新的民间文化传承方式之一,传统文化也通过这种方式被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所认知。对于当地人,体验式旅游产品赋予了他们将自己“祖传的文化”对外界进行重新呈现和表述的机会,这激发着如买买提艾力·玉素普一样的文化持有者,在文化体验过程中,重新回溯和学习自己习以为常的手艺和文化,重新认识和理解原生性文化的价值。文化发掘、文化展示、文化呈现的过程,也是提高当地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的过程。对游客而言,与过去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行为不同,体验式的旅游活动以更直接的方式引导着客地关系的互动。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了解,从“蜻蜓点水式”转向“深度接触式”。游客的需求倒逼旅游产品的提供者,发现更有深度、更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开发更具文化价值的体验式旅游项目也成为经营者的生存策略。此外,体验式旅游产品带来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文化场域中的“我者”与“他者”通过充分互动,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它引导人们从“主位”与“客位”、“内部”与“外部”的不同视角去认知、思考和讨论同一空间中的社会文化内涵,部分“城外来客”因为参与到文化创作中而对地方性文化产生情感依恋。
如今,老城的原住居民与来自不同地域的“新的老城人”共同生活在老城之中,他们共同建构着新的、更多元的社会结构与地方文化体系。喀什老城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老城人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社会支持。老城人在这个空间中思考如何将自己的生活转化为文化产品,置入旅游市场进行再呈现;外地游客来到这个空间,进行文化接触、文化观察和文化体验。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具有内生逻辑,“文旅融合的内在逻辑是旅游者个体参与创造文化旅游题材的过程,是文化旅游主体作为象征意义(符号)系统的文化旅游装置(客体)通过个体文旅消费行为进行创造、转换和连接的过程,是客体与主体之间‘唤醒’与‘沉浸’的统一,‘索引’与‘凝视’的统一。体现为‘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互动过程”。在旅游行为发生过程中,往往是文化为旅游市场提供内容,文化产业为旅游提供了产品,旅游则作为文化接触和促进交流的方式或渠道。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又催生了更多文化产品的创作与开发。“经济共益是文化共享的前提,文化共享是经济共益的支撑,旨在将旅游地建设成为居民与游客的共同家园。”
三、文化交互: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共同体意识的重构
在“活态保护”的理念下,喀什老城的改造以原生文化为主体,将当地人留在原本的生活区域,也留住了老城人的生活,留住了他们的手艺和生意,“保持旧城风貌”成为改造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人与遗产实际上是生命的共同体。保护遗产就意味着要保护人。”旧城旅游的吸引力在于,旅游目的地保留了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生活痕迹,保留了市井生活的气息。清晨洒水、浇花的“羊缸子”,放学后跑来跑去的小古丽和巴郎子,夜晚坐在门槛上聊天的老人,共同构图了喀什老城的生命图景。旅居喀什的画家国国认为:“经济与文化应该是同步发展的。能够将当地资源变现、为当地人增收,是一种发展。但不能因为商业的进入就丢掉了老城有声、有色、有味道的东西。文化断了,留下的就是一座只有建筑的文化空城。喀什老城改造比较成功的一点,是源于当地人还住在这个地方。我在这里能看到当地人的面孔,听到他们的乡音,看到他们养鸽子、在老茶馆坐着喝茶,就似乎能看到他们当年或者多年来生活的样子。”
一座城市的文化与当地的人和原生环境相适配。老城人“生于斯、长于斯”,当城墙之外早已高楼林立,他们仍然坚守着这片土地,坚守着祖业,形成了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吻合的文化观念和行动逻辑。同时,外来文化也给小城带来了新鲜空气。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在此交织,才成就了老城文化的动态性、流动性和高度的包容性。
“宽松的包容度为民间创造力的萌发提供了空间。”除了大量游客和商户的到来,喀什老城还吸引了一批文艺青年、文化学者和艺术家成为常住的“租客”。他们大多来自于外乡,在老城开设客栈、饮品店、工艺品店等,还有画家、摄影家、作家等旅居于此,从事与文化和旅游相关的工作。相对于游客,租客从时间维度上与原生文化的接触更多、更久,对当地文化的理解和融入程度更深。画家国国便是其中的一员。他来自乌鲁木齐,曾在上海生活多年,是一个著名咖啡品牌的画师。谈到留在喀什的原因和喀什带来的文化震撼时,他回忆说:“我有一个老哥,和我一起到喀什画画。我第一次来喀什,就被老城震撼了,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这里的人,是他们的笑。这里的小孩,年轻时尚的女孩子,还有老人,他们对陌生人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很甜很美的笑容,和大城市里的感受不一样。这种感觉要用心去体会的,是确确实实需要用文学词汇去形容的。一开始,我一直在想,啥时候走呢?在这呆多久呢?现在呆习惯了,可能下半辈子就在这儿了。”除了个性偏爱、文化震撼和与当地人的情感互动,国国的留驻还与一个社会组织的组建有关。“来喀什1个多月,我就开始计划组织‘速写喀什’活动,我把工作室也命名为‘速写喀什’。我们每周都举行画聚,主张大家用速写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城市和生活。”
初到喀什时,国国作为身处异地的异乡人,以“旅”和“游”的方式第一次融入异域,老城成为他了解当地文化的一扇“窗”。国国在老城这一文化场域中与当地文化近距离接触,浸淫于内在情境之中,同时,自身也成为地方文化体系重建过程中的贡献力量。国国之所以愿意久居于喀什,既有初遇时的文化震撼,也有“成为当地人”的文化适应,还有对“速写喀什”组织组建并与组织成员建立起密切关系的情感眷恋。旅游业的发展使主客关系的交互愈加频繁和紧密,“成为当地人”成为部分游客和租客的理想与情怀,“集体”的面向成为个体进行文化融入的依托。喀什的另一个次生文化群体——“喀漂”,正是在这种密切的社会往来关系中应运而生的。
“喀漂”是在喀什地区长期停留的一个外乡群体,群体内部成员多因喜欢当地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留下来工作、生活。“喀漂圈”虽小,却有内生的文化分层,以性别、年龄、职业背景、来源地等因素区分,形成了若干“圈内圈”。“喀漂圈”成员的文化共性是,对陌生环境和异文化的适应性较强。他们除了与次生的文化群体“喀漂群”交往,进行圈内互助,也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与原生文化形成互动关系,寻求当地文化的接纳和认同。
大大小小的文化圈层相互交织,形成了相对长期和稳定的主客关系,以及客地文化网络。作为“喀漂群”中一员的小强,在老城夜市“练摊儿”时与相邻的摊主相处非常融洽:“我的邻居特别热情。比如我要拉个电线,他们觉得我不会,就会立刻帮我弄好。那种热情程度,就好像我要找一个女朋友,他直接帮我把婚礼都办了,连孩子、孙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外乡人的进入和融入,使喀什老城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结构发生着变化。老城本地人与停留在老城的外乡人共同构建起新的社会共同体,原生文化与次生文化共同构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在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在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喀什老城文化重塑的过程中,国家在场的重要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对于老城改造工程的推进,国家巨大的资金支持体现出对项目的重视,而“一户一策”的改造方案体现出对居民主体性的尊重;其次,老城空间格局的重新规划和布局需要国家在场,它要求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具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第三,对AAAAA级风景区的管理和服务是持续性的,国家在资金、人力、政策等方面的不断投入,对于喀什老城的旅游发展和居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第四,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旅游家访户”的认定和政策性扶持,对于当地文化保护与传承,以及文化认同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老城改造项目的参与者许浩认为:“喀什老城一直处于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现在国家提出‘文化自信’,应该在老城中得到体现,老城应该为多种文化的交流提供更大的空间。举个例子,如果不是因为国国老师和王立军老师的指导,我的民宿设计不会做得这么好。艺术家留在喀什,对喀什的文化保护、延续和老城的文化建设都是有帮助的。王立军老师、国国老师也是老城文化群体的一部分。老城文化会影响他们,他们也会影响老城文化。”
“我者”与“他者”经过交流、博弈、磨合之后形成交融之态。佩里认为,同一地理空间中的个人,可能来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和职业背景,群体中的成员不断流入、流出,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正是在对异质性的不断协商中形成的。真正的社区整合,是“不贬低差异,不强加相同”。“所有成功的文化都有综合性的特点,只有不断与外界保持吸收、交流的状态,才能持久而不封闭”。
老城人生活在由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家庭组合而成的区域中,不同个体和不同家庭的文化不尽相同,但他们共同构筑了老城文化。老城的文化多样性不仅是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会关系整合的方式,是一组动态的、有生命的、变化的过程。文化多样性使人们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老城中,正是因为“不一样”所构成的多样性文化,促进着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社会发展和变迁,也丰富着多元的中华文化。
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需要整体性的视野。“人类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作为单纯的、每一个人都是从事其独自事业的一群个人而生存。”尤其是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今天,独在异乡的旅行者、艺术创作者,或者“喀漂”,都是无法孤立生活的,他们或多或少因为购物、饮食、住宿、工作等原因与当地人和周围环境发生关联。如果长期生活于异文化空间之中,人们往往会寻求或参与一个社会组织,使身份更合理化。比如“喀漂群”的组建和“速写喀什”组织的成立,它们使个人在陌生环境中寻找到组织的归属感。社会组织往往因为某种共性因素组合而成,或来自同乡,或年龄相仿,或兴趣相投,这些因素形成聚合人群的理由和张力,使外来之客找到能够长久留驻的情感依托。文化是一种“组织力量”。“个人”与“群体”的互动使社会结构中一个个原本孤立的“点”交织成网络,也从情感上使若即若离的散点式的个人对某个群体或地域产生依赖。这是人们在陌生环境中被接纳和认同的过程,也是喀什老城在完成旧城改造之后文化重塑的过程。
如今的喀什老城,是不同的人、物、文化在交往交融之后形成的新的文化空间,文化的不断学习和吸纳,使喀什老城中的文化元素更加多元多样。同时,社会结构也在文化磨合、碰撞之后更加趋于稳定。喀什老城地方性文化体系重塑的过程虽然没有地理上的空间位移,却在文化空间中进行了重新整合。老城中的“我者”,因为“他者”的到来接触到更多元的文化观念,“他者”也在理解、认同“我者”的文化之后,更加依恋这片土地。“我者”与“他者”共同建构起“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共同体意识也在频繁的交流交往中不断得到修正、调整和重塑。
四、结语
旧城改造不仅是房屋的翻新和建筑群的景观提升,也是对人文环境的再创造。通过历时12年的旧城改造、社会整合和文化重塑,喀什老城的人居环境从简朴走向精致,知名度从鲜为人知到享誉盛名。经过旧城改造和旅游开发的喀什老城,将当地人习以为常的文化元素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开发出更多样的文化产品,营造出多元立体的文化空间和文化与旅游交融交互的场域。
文化场域并非一个闭环,场域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场域中的“我者”与“他者”从“主位”与“客位”的不同视角对当地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交流对话,使处于散点式存在的个人,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及地方文化体系的重塑过程中逐渐被整合、被凝聚。
多元文化主体共同努力,创造出丰富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构建起具有一定思想共识的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共同体的形成催生着共同体内部产生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文化认同。共同体意识在交流交往中不断调整和修正,共同体中的个人也通过交流交往,强化着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